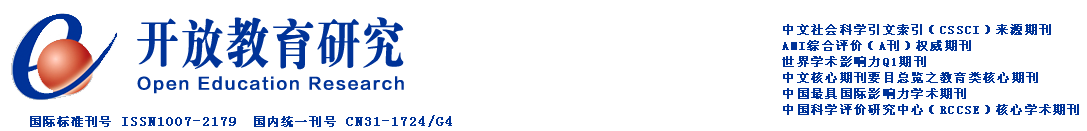郝德永
[摘 要]纷争与冲突是教育研究过程中的常见现象与棘手问题。许多关于教育问题的研究都伴随着两种对立的信条、立场、路径与方法的博弈。在两极之间进行“合理性”维度辩护、“正确性”维度选择,易使教育研究陷入没有出路的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教育研究的二元性逻辑、立场与方法使然。突破简单化思维,立足二重性原理,重构教育研究方法论,是教育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性与根源性问题。
[关键词]教育研究;方法论;二重性原理
[作者简介]郝德永,沈阳师范大学教授(沈阳110034)
遵循什么样的立场、逻辑与方法,是教育研究中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却是一个没能得到很好解决的根本性问题。长期以来,受制于二元性方法,教育研究往往热衷于在两极之间进行“合理性”维度辩护与“正确性”维度选择。于是,纷争与冲突成为教育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无疑,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无论选择哪一个维度,都难以赋予教育研究充分性依据与辩护性品质。只有突破简单化思维,超越二元性方法,立足二重性原理,重构教育研究方法论,才能使教育研究摆脱由来已久的纷争与对抗局面及困境。
一、二元性方法论与教育研究的逻辑性缺陷
教育研究应为人们提供清晰明确的关于教育的蕴含、意义、立场、信念、路线、方法等方面的解释。对于拥有悠久历史与庞大专业化队伍的教育研究而言,实现这样的社会期待,似乎并不是一件难事。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教育研究并没有做出关于教育问题明白无误的、富有针对性与完整性品质的解答。更为糟糕的是,种种明显具有逻辑缺陷的排斥性教育研究立场与方法,使人们经常性地陷入选择性困境。从古至今,许多教育研究中都充斥着大量的被赋予对立性品质的概念、原理、范式、路径等。“门派式”的研究风格、研究状态、研究路线、研究结论伴随着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困扰着教育研究活动。其根本症结在于教育研中根深蒂固的二元性方法论。
二元性方法论是经典社会科学研究普遍遵循的逻辑、立场与路线。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定位事物或现象的内涵、价值、功能、方法等,成为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模式。这种“用单一方式解决问题的思想已经在西方思想中占据了甚至可以称之为猖狂的主导地位。” [1]受制于二元性方法论,研究者普遍将各种整体的事物或现象尽可能地肢解、化约为微小的部分与要素,从中选择、确定“本质性”存在。对此,笛卡尔曾提出这样一条在任何时候都须严格遵守的方法论原则,即把“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而且适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2]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二元性方法论,“阻止看到(被它分割为碎片的)总体的东西和(被它消解的)根本的东西”[3],造成了对总体性、根本性、复杂性问题认识上的盲点与短视。二元性方法论在教育研究领域具有比较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许多教育研究者常常秉持主体与客体相分离、事实与价值相分离、个人与社会相分离、现象与本质相分离、历史与逻辑相分离的立场,导致其没完没了地在对立的两极之间进行选择、辩护与批判。教育这一系统化、“复数化”现象常常被缺乏常识地分割为种种简单化、单向度的存在。显然,将教育系统内部的某一个子项确定为教育的本质性存在,必然造成对教育的错位诠释现象,必然引起无休止的但却是“无解”的论争。如当我们一味地遵循机械还原论方法在知识、个人、社会之间确定教育活动的逻辑与立场的时候,对于恰切地定位教育活动不仅没有任何帮助,而且也不可能全面准确地阐释教育活动的内涵、价值与功能。但立足于二元性方法论的教育研究,顽固地坚持“不可修正、不可弥补”的立场,必然排斥与否定任何不同的理解与主张,致使所得出的每一种教育命题或结论,即使具有局域合理性成分,但必然含有自身难以克服的逻辑性缺陷。
二元性方法论主要表现在学术门派之间的纷争与否定。门派纷争是学术研究的普遍状态与倾向。在学术研究的历史上,尤其是在西方学术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研究者多是立足于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与解题方式,将各种复杂的自然、社会以及人的精神现象肢解后还原为唯一的、绝对的、普适性的结论。于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形成了众多的以各自的学术信条为轴心与支点的学术门派。而基于学术门派的学术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不可通约性品质。某一学术门派倍加推崇的信条、立场、标准、方法在另一个学术门派那里却可能是缺乏常识的表现。分歧与争鸣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式,但门派纷争却使学术研究更多地遵循固执一端、打击一片的排斥性立场与思维方式,是学术研究片面化、极端化现象与路线的始作俑者。它所造成的安置之道、归位之道、画地为牢现象,使学术研究沉迷于莫名其妙的分类癖好,执迷于在不可选择与无法选择的坐标体系中进行选择。门派纷争在教育研究中表现尤其突出。在近代以来的教育研究中,研究者通常立足于不同的学术门派展开论战,使教育研究领域被众多的、碎片化的门派之争所包围。从永恒主义教育流派、要素主义教育流派、进步主义教育流派、社会改造主义教育流派、存在主义教育流派,到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关于教育的价值、目标、内容、功能以及标准、模式等各个方面的理解与定位,均呈现出不可调和的两极化立场与指向。尽管每一种学术门派或许从某一角度能够“自圆其说”,具有指称范畴内的恰切性与辩护性,但总体上却均不足以诠释教育的本性与逻辑。五花八门的学术门派不仅使人迷失教育方向,且丧失对教育的识别能力、判断能力与驾驭能力。
二元性方法论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分析,而在于肢解,即将方法论意义上的多元分析方法演变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多元定位逻辑。阿尔文·托夫勒曾指出:“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4]受制于二元性方法论,教育研究者多习惯于用对立的方式进行思考,认为在对立的两极之间只有选择而没有调和与折中,而且拒绝任何形式的调和与折中。他们常常在不断强化、扩张自己的教育信条与领地的过程中,“把自己封在他们无法逃脱的‘确定圈’之内,因此,他们‘产生’自己的真理”[5],并将任何有悖于“自己的”真理的东西视为谬论。这种明显具有肢解性、破坏性特点的教育研究,必然造成种种本不应对立但却一直对立的“虚假对立”命题。诸如道德理想主义与社会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学生中心论与教师中心论、自主生成论与社会教化论、学科本位论与活动本位论等教育信条的对立,均肢解了整体的教育现象,消解了教育的同一性品质。显然,许多对立命题并不具备对立的逻辑基础或现实依据,在二者之间所做的任何选择,都难以赋予教育研究恰切的思维方式与路线,必然使教育研究陷入两难选择困境。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种种“虚假对立”的命题却构成了教育研究的基本框架与焦点问题。教育研究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表明,对于呈“虚假对立”状态的命题,不仅难以而且根本不可能以确定的方式做出终极评判。
二元性方法论的根本症结在于研究命题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缺陷。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常常在无限放大构成事物或现象某一要素的价值与功能的同时无视甚至否定其他要素的不可或缺性品质与地位,从而造成事物或现象的某些方面价值与功能被消解。于是,学术诠释仅仅局限于个别要素,没有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局限性。“这种分析的危险性在于两极对立的方式过于简单化,没有认识到双方有许多交叉重叠之处。”[6]受制于二元性方法论,有些教育研究者易遵循“非左即右”的极端化立场,为了抨击、驳倒对方,不惜以牺牲教育的丰富性、完整性、多维性为代价,窄化教育的要义、意义与功能,简化教育的要素、依据、内容与基础,使教育研究因对术语、命题与问题的诠释不足而拘泥于种种“缺失性诠释”,即只立足于某一背景与角度对教育命题进行单向度诠释。它只能论证制约命题的某一方面依据的必要性品质,却难以整体地把握相关教育命题的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内涵与依据。显然,任何一种“缺失性诠释”都只具有“有限合理性”特点,即使某种诠释可能比另一些诠释看似更为合理、更为可行、更为有效,但终究因其“天然性”缺陷而不具备恰切性品质。长期以来,二元性方法论不仅造成教育研究中的要素性、价值性及机能性缺失现象,使教育研究因种种“缺陷性诠释”而经常性地陷入“怎么诠释都有理,怎么定位都不对”的困境中。
二、“二重性原理”与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突破
超越二元性方法论是教育研究摆脱困境的基本途径。然而,尽管二元性方法论已声名狼藉,但在教育理论研究过程中,二元性思维、立场与方法并未终结,教育理论研究者也并未真正摆脱二元性方法论的困扰。因而,问题不仅在于是否要超越二元性方法论,而是如何超越二元性方法论。没有一种具有突破性品质的教育研究方法论,就不会有二元性方法论的退场与消失。而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突破关键在于由二元性方法转向“二重性原理”。“二重性原理”的精髓与要义在于遵循“既是……又是……”的结构化原则,摒弃“要么……要么……”的元素主义立场,强化关系思维与“双重解释”方法,使教育研究从根本上摆脱“非左即右”的方法论困境。
“二重性原理”的逻辑起点在于总体性方法论规则的建构,促使教育研究由元素主义研究范式转向总体性研究范式。系统的断裂与失衡,是教育研究二元性方法论恰切性品质缺乏的根源所在,解决断裂与失衡问题是教育研究“二重性原理”的立论依据与根本性旨趣。统一性是教育存在的基本品质,无论是就制约因素、理论基础而言,还是就内容、标准、方法而论,教育都具有不可还原性、分割性品质与特点。任何一个单质性因素只能构成教育存在坐标系中的一个坐标点,而不能构成教育唯一的、终极性依据。任何简单化的研究思维、立场与方法都会导致偏激的命题与结论,并造成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决策失误与失败结局。现代众多的教育理论流派就是因为缺乏对教育总体性品质的正确认识,致使教育研究面临着难以调和的纷争与冲突、遭遇强烈的抨击与抵触、陷入无穷的困惑与困境。现代国外众多的教育改革运动也是因为立足于残缺不全的、失衡的理论而使教育发展陷入屡改屡败、屡败屡改的困境。显然,维持教育系统的完整与平衡是教育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教育研究结论科学、恰切、有效的基本前提。
“二重性原理”的基本品质在于平衡,基本逻辑在于平衡,基本旨趣也在于平衡。平衡是“二重性原理”的逻辑起点,是“二重性原理”的落脚点。在教育研究过程中,总体性方法论规则要求教育研究者遵循“既是……又是……”的原则,坚持从坐标点的漂移转向坐标系的构建,从两极转向中介,超越在教育系统的构成要素之间确定立足点、寻找归宿的思维与做法,消解那种一味地在处于博弈状态的两极之间进行排斥性选择的研究逻辑与方式,把那些看起来独立存在或彼此对立的要素整合起来,恰切地处理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平衡关系,既不使某一要素孤立于整体,也不使各个要素相互孤立。
“二重性原理”的基本路径在于坚持结构化原则,促使教育研究由“实体思维”转向“关系思维”。在教育研究过程中,一个十分突出且常常被忽视的现象是,研究者在刻意解决某个问题的同时却引发种种新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实体思维”使研究者缺乏结构化立场,无视教育的理论来源、制约要素、价值、目标、内容、方法的总体性品质。“实体思维”的基本理论假设是事物或现象可以尽可能地被还原为一个或一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彼此之间不仅在空间上是分离的,而且各自的性质也是彼此独立的。这种思维的首要错误是“假设我们能够把某些要素从整体中抽取出来,并可在这种分离的状态下认识它们的真相。”[7] “实体思维”试图在教育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追究与定位,严重阻碍或妨碍人们认识与领会教育的真相。如立足于社会实体论的教育研究,将社会结构定位为教育研究的出发点,强调社会结构的客观性与决定性品质。而立足于个体实体论的教育研究则将个体行动定位为教育研究的出发点,强调个体行动的动机、意义与价值的首要地位与决定性作用。显然,无论是个体实体论还是社会实体论,都没有为教育研究找到一个恰当的起点,错误地将个人和社会分割开,“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当前所流行的‘个人’的概念所指的,似乎总是存在于社会‘之外’的东西;而社会这个概念所指的,似乎也是超然于个人之上的东西。好像人们只能在两种理论之间进行选择。”[8]事实上,教育的真相恰恰存在于被“实体思维”武断地割裂为种种呈对立状态的各个部分或元素的关系之中。在教育系统中,各构成要素相互制约、缺一不可。摆脱二元对立与冲突,关键在于突破“实体思维”的窠臼,转向“关系思维”。在教育研究过程中,“关系思维”要求教育研究者明确教育作为一种“关系”存在的实质与真相,相互关联地认识与定位教育,将作为教育存在的各组成部分或元素还原为教育实践关系网络中的一个个“节点”,超越脱离“关系”而孤立地以“节点”为依据定位教育的立场与方法,终结二元论的“要么……要么……”立场,消解教育各个构成要素的“虚假对立”状态。
“二重性原理”的基本方法在于坚持辩证否定立场,促使教育研究由一元化解读转向“双重解读”。“双重解读”方法的立足点在于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的整合,消解“打倒一个另立一个”的解读方式,“既吸取每种解读的长处,又避免每种解读的毛病。”[9]“双重解读”既指向研究的性质,又指向研究的方式。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双重解读”意味着教育研究既是价值性研究又是事实性研究,二者并非排斥性的、可选择的矛盾体。教育无疑是一种价值性存在,其研究性质与逻辑不同于自然科学。普适性规范、精确性标准、技术性方法一直作为衡量教育研究是否严谨、科学的基本依据。研究者总是迫不及待地、挖空心思地寻找普适性的教育规律。但这种以对客观规律的证实为主旋律、以真正的科学而自诩的教育理论,因其导致僵化、刻板的教育运行机制而遭遇失败。因而,教育研究必须摆脱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的逻辑与原则。但超越自然科学的逻辑与原则,并不意味着教育研究完全走向主观主义的立场与方法。价值性存在并不否定教育的事实性存在。那种完全否定客观性立场、定量与实证方法的主观主义研究范式,同样会导致教育研究的失败。教育的多维性存在品质决定了教育研究既有客观逻辑性解释,也有主观经验性解释。就研究的方式而言,“双重解读”意味着教育研究的“视界融合”,即不同视角与信条的相互融合与互补。教育的复杂性品质决定了教育研究视角与解读方式的多元化。而基于不同视角的解读,必然具有局域的合理性特点,但同时也必然具有整体的局限性问题。因而,对不同视角的解读进行对与错的裁定,在理论上缺乏辩护性,在实践中缺乏可行性。“双重解读”要求教育研究者超越“门户之见”,消解霸权主义、中心主义与排他主义的解读方式,使基于不同视角的各种解读都具有辩护依据与存在空间,使教育研究由相互否定与排斥转向相互对话与协调,通过“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解释者与解释者的对话”[10],促进不同的解读消除偏见、跨界融合,实现各自的改进与完善,使对教育的解读达到一种新的视界。
参考文献:
[1]小威廉·多尔.杜威的智慧[J].全球教育展望,2001,(1).
[2]M.巴诺夫,B.彼德洛夫. 科学逻辑与科学方法论名释[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124.
[3]埃德加·莫兰. 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9.
[4]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 从混沌到有序[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5.
[5]保罗·弗莱雷. 被压迫者教育学[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序言.
[6]阿伦. C. 奥恩斯坦,等. 当代课程问题[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6.
[7]大卫·雷·格里芬. 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55.
[8]安东尼·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26.
[9]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7.
[10]王治河. 后现代主义的建设向度[J]. 中国社会科学,1997,(1)
On "Duality Principl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Hao Deyong
Abstract:Strife and conflict are the common phenomena and thorny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Many researches on education are coupled with the game of two opposing creeds,stands,paths and methods. The defenseof "reasonable" dimension and the selection of "correct" dimension between the two poles make educational research repeatedly get into trouble.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e binary logic,stand and method. Breaking through simplistic thinking method,being based on the duality principle and re-constructing methodolog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re the fundamental and original issue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Key words:educational research,methodology,duality principle
Author:Hao Deyong,professor of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本文系作者发表在《教育研究》2013年第11期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