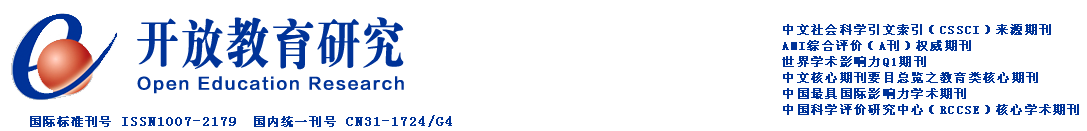在经验研究中,是否有良好的质感,直接影响研究的效果。有了经验质感,往往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问题意识,发现经验的意外,较好地把握经验的内在机制。
一.何谓经验的“质感”?
一般而言,经验研究包括两个步骤,一是对经验现象的体悟,二是对经验材料的分析。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后一个步骤,以为准确地获取材料,科学地分析材料,就可以做一个好的经验研究,经验化约为材料,研究简化为对调查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殊不知,缺乏了对经验现象的体悟,再科学的经验材料的分析也有可能是离题万里的,要么是不符合“常识”,要么就仅仅是一个“常识”:前者的意思是说经验研究严重脱离现实,不合逻辑;后者的意思是说经验研究没有发现,没有知识增量。
我们说,经验本身是要训练的,主要不是指对调查方法和分析工具的掌握,而是指对经验现象的体悟能力的训练,即培养经验的质感。什么叫做质感?质感首先意味着整体感,能够恰当地将任何一个经验现象放置一个更为宏观的社会体系中去。比如说,各类人群自杀率的不同,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在支撑,妇女、尤其是年轻妇女自杀率高的地区,往往发生在宗族性村庄中,因为这种类型的村庄结构,年轻妇女处于弱势地位;老年人自杀率高的地区,往往发生在原子化的村庄中,因为老年人在这种村庄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但是,自杀统计往往不会涉及村庄结构,因此,调查方法再高明、分析工具再先进,也很难把握中国农民自杀的这一重要机制。
其次,质感意味着敏感性,能够在一个具体的研究场域中发现经验的意外,即场域内经验现象之间的悖论——这个意外是因为研究者有了下意识的现象之间联系的假设,经验稍有不同,即可感觉到。“原子化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弱”是经验的“常识”,一旦有原子化村庄内农民合作很好的现象,有经验质感的研究者可以立马感觉出来,通过增加变量来解释现象之间的悖论:比如,村庄有无价值生产能力、行政能力是否强大等对集体行动大有影响。
再次,质感还意味着经验现象的延伸能力。这种延伸能力是整体感和敏感性的综合,很多有过长时间民族志调查经历的研究者都有这个体会,到一定程度,发现对村庄的任何方面都很熟悉,被访谈对象“只要说一句话,就知道他下一句说什么”,这是有整体感的表现,也是敏感性不足的表现,经验质感超强的研究者,可以通过对经验现象的延伸能力来解决这一问题。正常情况下,研究者在分析现象A时,可能与B、C两个现象建立联系,A、B、C三者之间建立逻辑关系,并形成一个现象体系,换言之,对研究对象A的延伸,只进行了两层:由A到B,再由B到C。但如果能再进一层,到达D,且将A、B、C、D四个现象建立了另一个更为复杂的现象体系,那就意味着经验质感更增强了一步。
二.经验的理论提升
经验质感是一种经验现象的处理能力,集中表现为对经验现象的理论提升能力,包括问题意识、概念化及中层理论三个方面。
能否提一个好的问题,综合反映了经验质感。好的问题不能仅仅是一个经验的常识,也不能不符合常识,好比说,这几年媒体不断报道农民维权事件,然后就提出一个学术命题“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说这个命题只是解释农民为何会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这是一个常识,因为这几乎只是在说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说这个命题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农民有了公民政治诉求,那么,这不符合常识,因为绝大部分维权事件都仅仅是获得物质利益,并无政治要求;但是,如果说这个命题是要解释当前农民维权事件与上世纪90年代的不同,发现了一些新因素,比如,钉子户更容易在媒体的配合下进行抗争表演,则它是一个真命题,既符合常识,农民确实为了一己私利(而非政治诉求)敢于抗争,又超出了常识,看似普通的现象实际上有了新内涵。很显然,假使农民维权事件是现象A,农民趋利现象及政治诉求是现象C,媒体介入是B,那么,前两个假设之所以是假问题,是因为没有一个整体感,无法将A准确放置由A、B、C共同塑造的政治结构中,也没有敏感性,未能发现近些年A现象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的异常之处,更无现象的延伸能力,连关键变量B也没有延伸进来。
概念化的过程是描述、解释现象的过程,前提是在现象之间建立正确的联系。没有经验质感的研究,很容易在经验现象之间强行建立联系,尤其是没有问题意识的时候。比如,现在的很多经验研究都是应景式的研究,其问题意识并不是从自己的经验质感中产生的,而是从宏大理论或媒体话语来的,研究村民自治的时候,自然地找到民主理论,研究农民维权的时候,自然找到公民政治参与理论,硬梆梆地虚拟出了现象C,以此来解释现象A,建立A、C之间的联系。注意,建立现象间正确联系的第一步是切忌似是而非地引入一个现象:在一个有具体研究场域的经验研究中,任何一个现象都必须从这个场域中来,而不能从理论或其它的研究场域移植过来。
即便现象C确确实实存在,还存在一个问题,A、C两个现象相隔太远,但解释链条却很短,一定会抹平其它的可能更重要的变量B。因此,正确建立两个现象之间联系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要在两个最相近的现象之间找联系,而非舍近求远。假如现象A、C之间有联系,那么,应该先解释相邻的现象A、B之间的联系,再解释另一对相邻的现象B、C之间的联系。
现象之间的正确联系建立起来之后,就需要描述和解释,描述和解释出一个结果出来,就有概念化的意思了。本质上,任何概念都是内含的多个现象的集合,比如“差序格局”这个概念,它至少是中国人群己界分、长幼有序这两个现象之间的集合,由于中国人的行动单位是家庭、家族等群,而非个人的己,使得群的内部构造了一个等级秩序,这两个现象高度联系,且构成了与西方“团体格局”不一样的结构。
如果说概念化是具体的多个现象间联系的描述和解释,那么,中层理论就是多个概念间联系的描述和解释,中层理论的形成一定会有概念化的过程,但概念化却不一定会形成中层理论。同样以“差序格局”为例,费老在提出这一概念的时候,只有概念化过程,只是对具体现象的描述,但是,此后很多关于中国社会现象的研究,进行了多种概念化的努力,相互之间却都可以在差序格局中找到位置,比如,圈层结构、行动单位、关系等,很有可能,差距格局就变成中层理论了。而一旦成为中层理论,其解释力将大大拓展,可以解释更多的经验现象间的联系。
三.理论的现象还原
实际上,质感的作用不仅仅表现在经验现象的理论提升能力上,还表现在理论的现象还原能力中,在经验研究中,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经验现象的理论提升过程,也是理论的现象还原过程。
一个真正有经验质感的研究者,所提的好的问题意识,不仅在经验上经得起推敲,还在理论上经得起考验。同样以“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这一命题为例,很多人用抗争政治理论去套,却不知道这一理论的原型:政府行为、集体行动、抗争三个现象之间的联系。以为农民有了集体行动,或者有了反抗行为,就是一种抗争政治,殊不知,抗争政治不仅需要集体行动,还需要政治性和专业化,缺一不可。如此,要用这一理论,就应有一个整体感,即由中国政府行为、农民集体行动与农民抗争构成的政治结构是怎样的,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体性事件、农民集体上访等现象放置一个恰当的位置,也需要敏感性,发现这些现象在抗争政治这一理论脉络中的悖论,与西方现象的不同之处,也同样需要现象的延伸能力,将一些关键的变量如市场化媒体的作用引进来。似是而非地用任何一个理论去解释鲜活的经验现象,不仅无法解释这些现象,也无益于推进理论的发展。
尤为关键的是在概念的使用上。概念不是用来简化现象解释的,而是为了更好地解释现象,在现象足够复杂,而概念无法统摄时,需要修正的是概念,而不是现象。同样举用抗争政治理论解释农民集体上访现象的例子,当研究者面临着这样一个困惑,即很多时候地方政府表现得极为软弱、无奈,但却又经常表现得过于暴力时,那就需要仔细辨析“政府”这一概念,它至少有两个属性——管理机关和暴力垄断者,任何一个属性都不足以把握政府这一概念的内涵。这些年来,在解释农民集体上访现象时,很多研究把地方政府描述成是一个冷血的暴力的独裁者,这要么是一个宣传策略,要么是没有一点概念的现象还原能力,结果都是简化了现象解释。
把概念还原成现象及现象之间的联系,是考虑概念适用性的前提。一个从不考虑概念适用性的研究者,肯定是理论的教条主义者,谈不上经验质感;很多人在使用概念时,考虑其适用性并不是从具体的经验研究出发,而是简单地借用别的研究成果(大多是理论的注释),这是一种偷懒行为,假的经验研究者。
至于说中层理论,其现象还原能力主要表现在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中。在社会学研究中,估计很少人怀疑西方理论本土化的必要性,这说明社会学确实是一个经验研究为基础的学科。但是,对本土化的路径却有不少争论,主要表现为到底是从理论到经验还是从经验到理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实际上,经验现象的理论提升和理论的现象还原本是一体两面的双向运动,人为地将两者割裂开来,只能说经验和理论的训练都还不够。
四.经验质感的培养
一个长时期做经验研究的学者,不一定有经验质感,其中的奥妙何在?这得从质感的三个方面谈起。
如果经验研究化约为对材料的获取和分析,那几乎永远建立不起质感,因为它失去了对经验现象的体悟过程。同样是访谈,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方式,一是访谈仅仅是资料收集方式,尽量追求材料的完整性、客观性,似乎被访谈者只是材料的储藏器,生怕访谈者的某句话、某个动作影响了被访谈者的情绪,导致材料的失真;二是访谈过程本身是经验研究的一部分,材料本身不甚重要,重要的是访谈者与被访谈者在获取、理解材料过程中的互动,尤为注重某一具体的材料在现象联系中的位置,材料的完整性并不来源于细节,而是来源于其在现象体系中的明确定位,材料的客观性也不来自于被访谈者是否真诚,而是来自于材料间的相互印证。很显然,前一种访谈方式是很难培养质感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调查方式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它是否认经验研究是有人文主义色彩的,而非纯粹的科学。
质感的首要特征是整体感,因此,将经验现象化约为碎片化的材料,不是一个合理的做法。相反,应该尽量理解某一具体材料与前后左右的联系,注意,关键在联系,而非孤立的材料。对于培养质感而言,材料再详细、再客观,如果无法准确定位,那也是枉然。比如,你在调研中准确得计算出农民种田的投入是300元/亩,产出是1000元/亩,如果不计算其投入产出比,并与家庭结构等因素相联系,这些数字再准确也是没意义的。对于老人农业而言,这个数字或许是很可观的,但对于壮劳力经营的农业而言,这个数字却有可能是让人失望的。当“可观”、“失望”这些类似的主观评价出来时,就往质感迈进了一步。
敏感性建立在差异、悖论上,因此,对质感的培养还意味着要不断、甚至是重复解释现象之间的各种可能的联系。再举“原子化村庄集体行动能力弱”这个例子,研究者到任何一个村庄调研,都尝试去验证这一联系,最后发现,即便这个联系是成立的,实际上不同村庄有不同的逻辑,解释得越多,发现变量越多,内在的联系机制就越复杂,把行政因素、价值生产能力等因素考虑进去,就会发现原子化的村庄结构与集体行动能力这两个现象之间,有N多种悖论,可以建立出N多种联系出来。由于对原子化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问题极为熟悉,形成了下意识,一旦有现象的悖论发生,很容易就感觉出来。
现象延伸能力的培养,通俗的话说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以这样认为,经验本身是完整的,因此,理论上,任何两个现象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只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的差异。整体感意味着可以将一个具体的经验现象界分出几个部分,并大致确定各部分在现象体系中的位置,敏感性意味着发现两个现象之间的新联系,而现象延伸能力则意味着透过这个联系发现新现象,并最终确定这个现象在现象体系中的位置。比如,假如研究者在原子化村庄与集体行动能力弱两者之间建立了强联系,那么,研究者或许就容易依此发现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村庄灰色化问题等相关现象。一旦假设了这些现象会存在,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进行论证,这又回到了敏感性的建立过程中:对悖论、差异的解释。
说到底,经验质感不是别的,是对现象之间联系的把握能力,经验研究的最重要的价值是发现新的现象之间的联系。在经验研究中,这种能力可以部分地为分析工具取代,但是,好的问题意识,经验的意外,从来都产生于对经验的体悟过程中,而无可能从分析工具中产生。
原文载于《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