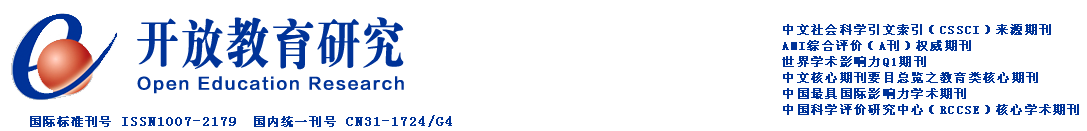余欣
在我看来,写本文化不仅应该包括写本学与书籍史研究,更应注重以写本为书写载体的知识传统的成立诸相的探究。表面上是以物质形态的写本为核心,真正的文本创制、知识传播、信仰实践的中心环节,却是书写者与阅读者。
写本文化研究,原本是非常冷僻的学问。近年来突然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甚至有构架甚为宏大的国际合作项目,从梵文写经、死海古卷、埃及纸草文书、泰米尔碑铭,直至明清稿抄本、批校本,但凡手写文献,无所不包。愿景十分令人鼓舞,但又多少给人以茫无涯际的感觉。不过,我觉得在积累研究个案的基础上,进行世界写本文化史的综合研究,或许是值得尝试的新领域。
以往的写本研究大体不出以下两个维度:文本内容考释和物质形态研究,后者亦称为写本学,或被纳入书志学的范畴。随着研究的深入,原先专攻写本学的学者,开始致力于综合考察二者的关系。所谓写本文化,表面上是以物质形态的写本为核心,真正的文本创制、知识传播、信仰实践的中心环节,却是书写者与阅读者。
皮埃尔-西尔万·菲利奥扎教授的演讲(载2014年12月26日“文汇学人”),不仅让我们获得了许多关于传统印度的抄写匠职业的新知,而且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和印度写本文化比较研究的广阔前景。尽管存在文献的年代落差,但是由于写本文化的共通性和延续性,这种比较研究依然是可行的。我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菲利奥扎教授指出,传统印度写本的抄写方式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根据梵学家的口述听写,还有一种是根据原本抄写新写本。不论哪种方式,都有可能造成一些讹误,因此在他们的题记中,有时会请求读者宽容他们的过错,行业中也流传一些诗歌描述他们的艰苦工作。这两种写本的作成方式,固然是普遍性的类型,在世界各写本文化中也是最为常见的,但是菲利奥扎教授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有意思的资料细节。
在敦煌写本中,我们可以找到颇为相似的例证。例如,自大中九年(855)三月份开始,法成在沙州开元寺讲《瑜伽师地论》,直到大中十三年末或大中十四年初去世为止,大约一个月一两卷,听讲弟子有智慧山、谈迅、福慧、法镜、一真、洪真、明照、恒安等,部分弟子听讲《瑜伽师地论手记》与《瑜伽师地论分门记》的笔记本在敦煌藏经洞中保存下来。S.5309《瑜伽师地论》卷三十题记:“比丘恒安随听论本。大唐大中十一年岁次丁丑六月廿二日,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于沙州开元寺说毕记。”对于抄写错漏之处,敦煌的抄写者,也会写上一些自谦、自责或自辩之词,在著名的P.3780《秦妇吟》写卷末尾,我们可以读到学士郎马富德自称“手若(弱)笔恶,若(多)有决错。名书(师)见者,决丈(杖)五索。”对于辛苦的抄写工作的抱怨,敦煌也有不少有趣的诗作,例如净土寺学郎员义写完《事森》后,题诗一首表达对待遇太差的不满:
写书不饮酒,恒日笔头干。且作随宜过,即与后人看。
关于职业抄写者的类型及其社会地位,菲利奥扎教授从经籍抄写匠和公共抄写匠的不同特点做了分析,并且对其中较为特殊的皇室抄写匠的职责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做了很好的揭示。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同样可以从几个方面提供比照。唐代也有职业抄写者,叫做“写经手”或“写经生”,简称“经生”。除了抄写佛经外,还抄写儒家经典,并兼抄官府文书。在敦煌出土文献中,包含一批唐代长安宫廷写经,卷尾有格式严整的写经责任人名录,如敦博第55号《妙法莲华经》卷六:
咸亨三年二月廿一日经生王思谦写
用纸二十张
装璜手解善集
初校经生王思谦
再校经行寺僧归真
三校经行寺僧思道
详阅太原寺大德神符
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
详阅太原寺主慧立
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
判官少府监掌冶署令李德
使太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
详细罗列了抄经的时间、抄经者、用纸数量、装潢者、初校者、再校者、三校者、四位详阅者、监制者。其中设有代表皇帝的写经使专门负责监察,由当时著名学者兼高级官员虞昶(大书法家虞世南之子)担任,可见郑重其事。长安宫廷写经严密的制度设计,远远超过印度皇家抄写者,但是后者还要根据皇帝的命令起草文书,参与国家政事决策,这种政治功能是前者所不具备的。
与印度的经籍抄写者主要为梵文学者工作不同,在敦煌还有另外一种为政府主导下的大规模佛经抄写事业服务的抄手。贞明六年(920),夏五月十五日,归义军节度使府令沙州僧俗抄写《佛说佛名经》《贤劫千佛名经》百余部,祈愿城隍安泰,百姓康宁,府主己躬永寿,继绍长年,合宅枝罗,常然吉庆。
为人代写契约、书状等法律或实用文书的职业公共抄写者,在敦煌也是大量存在的。这也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类是官府中的书手,因为他们比较有文化,所以也经常承担本职以外的抄写事务,诸如抄写佛经或其他经典。例如S.4295《般若波罗蜜华咒》等诸佛经杂咒题记中的“押衙知三司书手吴达怛”,而P.3906b《字宝碎金》题记并诗的抄写者吕盈的身份是“伎术院学士郎知慈惠乡书手”;还有一类是活跃在民间的社会经济和法律事务中,我们在相当多的契约中,发现是由职业抄写者代书的。此外还保存了很多作为习作的契约抄本,实际上就是为了学习这类实用文书的教育实践的遗留物,目的是掌握将来为人代书必备的知识和技能(用字、书法、格套等)。
在敦煌,有一部分抄写者纯粹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而专注于佛经抄写。这种情形普遍存在,可以看作是佛教功德观念的产物。比较极端的例子,是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有一位八十三老翁刺血和墨,手书多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称愿流布沙州一切信士,祈愿国土安宁,法轮常转。且云以死书之,乞早过世,余无所愿。但也有相当多的抄写行为是为了谋生和商业利益,因而抄写者的报酬,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另外一件《秦妇吟》写本S.692,金光明寺学仕郎安友盛题记:“今日写书了,合有五斗麦。高代(贷)不可得,环(还)是自身灾。”李盛铎旧藏《雍熙二年七月十日记事》,则记录了抄写者的酬劳是皱皮文鞋一双。
至于与书写有关的图像学资料,在中国的墓葬壁画和传世书画作品中,也有很多反映,此处不赘。
总之,从写本的制作者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的思考,让我们对写本文化的内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在我看来,写本文化不仅应该包括写本学与书籍史研究,更应注重以写本为书写载体的知识传统的成立诸相的探究:知识的创造、复制和改编的过程,知识传播与知识控制的方式,文本辑录的选择性所隐含的文化心理与文化象征,宗教仪轨、信仰观念、意识形态的渗透及其影响,个体情感与思维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等维度,重新思考写本文化在社会史、思想史和文明史上的意义,尤其是知识建构与文本形态、书写行为、使用实践之间关系的省思。
展望未来的课题,以中国敦煌吐鲁番文献、日本古抄本、印度写本及相关图像资料进行整合性探讨,写本物质形态与知识社会史研究齐头并进,写本文献和刻本文献研究上下贯通,以此观照传统亚洲学术-信仰-制度成立史之诸面相,追索其内在的腠理,重绘其变幻云图,进而构建写本研究及东西方知识传统的“交错的文化史”,并藉此对写本于文明的意义进行博观与省思,相信不仅可以拓展传统社会书写文化史与知识史诸领域,亦有资于推进世界文明史研究。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文为作者对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西尔万·菲利奥扎的讲演《传统印度的抄写匠职业》的评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