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部英国电影故事片,原名叫Sixty Glorious Years(意思是:辉煌的六十年),描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英国六十余年的事迹。它的中文译名叫《垂帘六十年》。这就产生了中国与西方文化传统的错位感。中国封建时代在特殊情况下,太后或皇后临朝听政,殿上用帘子遮隔着,叫“垂帘”。如唐武则天、宋刘太后、清慈禧太后,都有过为幼主辅政而实行“垂帘听政”的历史。但是,英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垂帘听政”的政治现象。而且,维多利亚女王上台就是亲政,并没有什么未成年的幼主要她来辅政,叫什么“垂帘”?这类翻译中的文化传统错位现象,时有发生。这牵涉到翻译的“归化”和“外化”如何平衡的问题。
鲁迅在谈到翻译工作时曾提出:“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
笔者主张坚守“归化”和“外化”(保存洋气)的分寸即掌控二者的平衡。举个例子: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20首中有句“with shifting change,as is false women’s fashion”,有人译作:“轻佻女人,朝秦暮楚。”但莎翁头脑里不会有中国春秋战国的影子,因此在沙翁作品的译文中出现“朝秦暮楚”这样的成语,就形成了中西文化的错位。(如果换一个成语:“水性杨花”,岂不更好?)但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绝对化,认死理。
公元前二十多个世纪时的古埃及人不知道中国的方块汉字。公元前二千年的耶路撒冷城里,以至整个罗马帝国中,没有人知道方块汉字。那么,Pyramid译为“金字塔”,cross译为“十字架”,这能认为是文化错位吗?不能。因为如果这样来要求翻译,那么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整个地成为不可能,理由是原文和译文本来就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产物。而且,就这两个译词而言,没有更好的译法可以替代。而这两个译词的特点恰恰是汉字“金”的形状和汉字“十”的结构。我们可以用中国成语“惟妙维肖”来形容这两个译词的恰当。
2. 人名、地名、国名等的翻译,最好是根据原文的音来译,这叫“名从主人”。例如London译作“伦敦”,NewYork译作“纽约”,都准确译出了原名的发音。但是,有的译名是长期沿袭下来的,原名的读音或译名的读音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了变化,变成不那么吻合了;或者,原名和译名的读音本来就不吻合,那么,要不要改动呢?我以为不宜改动。比如,“莫斯科”原名MOSKBA(俄文),按理应读成“莫斯克伐”。但中文译名“莫斯科”是根据英文Moskow来的,已形成习惯,不能更改。又,“旧金山”的原地名是SanFrancisco,若译作“圣弗兰西斯科”,当然可以,但不能废弃“旧金山”,这个地名源于当年华人到此淘金的历史。Portugal,读音应是“葡萄葛”,怎么译成“葡萄牙”呢?原来最早译此名的是一位福建人,他的方言中“牙”读音就是“葛”。还有一种有趣的音变现象,比如,有的译名出现增字(音)现象,有的译名却出现减字(音)现象。如Russia(用英文代俄文,二者对等)读作“罗西亚”,却译成“俄罗斯”,这个增加的“俄”字是R发音时带出的气流次音,原可忽略不计。而另一个,America,读作“阿美利加”,却译成“美利坚”,把“阿”字减去了。这两个译名,在译音时有增有减,颇为“自由”。
有时,同一个地名有两个译名。如意大利城市佛罗伦斯,又译翡冷翠。原来前者译自英文Florence;后者译自意大利文Firenze。翡冷翠这个美丽的译名出自诗人徐志摩的手笔。
还有一种张冠李戴的现象。England,读作“英格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核心部分)而不是全部。但它又可指英国全部,是“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同义词。这个England的中文译名叫“英吉利”。“英吉利”其实译自English,那是“英语”“英文”“英国的”的意思。上面提到的“美利坚”,其实译自American,那是“美国的”、“美洲的”的意思。这些,能给它们扣上“误译”的帽子吗?不必,也不能。
由此可见,有了一条原则,应该遵守。但又不能一刀切,不能强制推行。已有的译名,已经约定俗成,是不能更改的。
3. 中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全面推广普通话。当然,并不废止方言。联系到名词的翻译,就会引起一些想法。Sofa译作“沙发”,用的是上海方言发音。上海人读“沙”为so。按普通话,“沙”读sha,不读so。又,Washington译作“华盛顿”,也是用的上海方言发音。“华”上海音为wo,恰合英文原词的发音。“华”按普通话读作hua,这就不合原词的发音。英国诗人Shelley读音应为“谢利”,但译作“雪莱”,不可更改。原来上海口音“莱”相当于ley。而且,作为诗人名字,“雪莱”比“谢利”美。Alexander Dumas译作“大仲马”,而原词中怎么也发不出“仲”字音来。Du按法语发音勉强可以“杜”代。但是“大仲马”出自林纾琴南先生的译笔,他是福建人,福建方言发音“仲马”接近法文的Dumas!柯南·道尔的探案作品的主角名字叫Holmes,应译成“霍尔姆斯”。但为什么译成“福尔摩斯”?这也是林纾的译法,原来福建方言读音中的辅音f都读作h,所以“福”读作“霍”!莎士比亚的剧作TheMerry Wives of Windsor,朱生豪先生译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Windsor怎么译成“温莎”呢?原来中文“莎”字有两读,一读shā(沙),一读suō(梭)。“温莎”的“莎”读shā,恰与原文吻合。但一般读者和某些演出该剧的演员都把“温莎”的“莎”读作shā(沙)了。还有,英国古代的绿林好汉RobinHood,读作“罗宾·胡德”。但现在通行的译名是“罗宾汉”。这也是上海(或吴地)翻译家的创造。“汉”字沪音接近hoo,而用“汉”译这位好汉就比“胡德”恰当得多。这位译家真聪明!
在推广普通话的时代,不能把已有的约定俗成的译名推倒重来。我们要尊重已经形成的传统,维护公众已经养成的习惯。
4. 翻译,在人类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很多人不了解翻译的重要。有人以为翻译很容易,只要手头有一本词典就万事大吉了。这是对翻译的无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上,作协领导所作的工作报告,往往不提文学翻译,这是对翻译的无视。如果不认识翻译的作用,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鲁迅称翻译工作者为普罗米修斯,这是极为准确的比喻。如果没有普罗米修斯,人类就没有火种,将永远生活在黑暗中。如果没有翻译工作者,人类面对上帝为巴别通天塔而降下的天谴,就不会有解救的良方,将永远生活在老死不相往来的蒙昧中。
当今是全球化时代,是信息爆炸时代。尽管英语是许多国家认可的通用语,尽管汉语是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而且通过孔子学院在各地的建立,汉语正在向全世界普及),但世界上还没有产生一种全球通用语。柴门霍夫创造的Esperanto(世界语)推广无效,原因是它是人为的,没有根。退一步说,即使Esperanto普及了,而各民族的语言并没有消失。从民族语言变成Esperanto也要经过翻译,不用说各民族语言之间的交流了。因此,翻译的功能仍然是人类心灵与物质交流不可或缺的工具,翻译本身即是推动人类生存和进步的一种重要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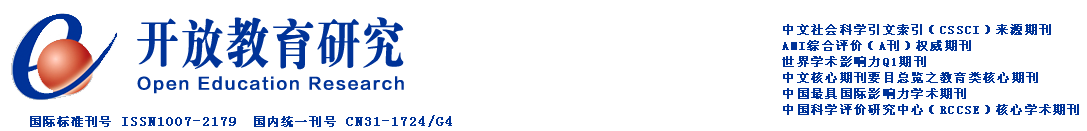
屠岸:译事四则
发布时间:2014/5/23 10:5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