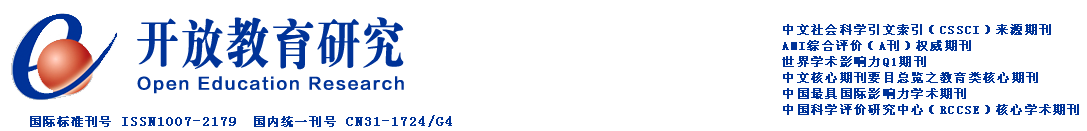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717 次 更新时间:2014-08-02 10:21:02
● 李文倩
李幼蒸先生的《忆往叙实》(重庆大学出版社二○○九年版)一书,自二○○九年出版以来,即遭到两种意见截然相反的极端评价。而招致极端评价的主要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在此书之中的一些回忆性文字中,坦率地表达了对某些著名学人的道德非议。而这样的非议,在中国当代的回忆性写作中,其实是不多见的。在中国,为贤者、尊者讳,有着漫长而悠久的传统,而“当代”作为传统的一种延伸,自然也少有例外。二是作者在此书中,坦率地表达了他对人文学术问题的一些反思性意见,其中有对某些当代学术思潮及动向的尖锐批评。或许在某些读者看来,这样一种写作有违温柔敦厚的美学原则,因此而显得不甚厚道;但如果我们真正将学术视为天下之公器,则此种开诚布公地表达自身意见的方式,当有其积极意义。而且,作者在书中所讨论的一些大的学术问题,在今天仍有反思的必要,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相当迫切。
一
百年学术的核心议题,即学术现代化问题,而此问题之所以紧迫,是因为传统的学术资源无能为急剧变革的社会提供思想上的支撑。而学术现代化的问题,在其最基本的层面上,即意味着我们如何对待西方学术。一般的学术态度是,向西方学习从而赶超西方,这当然不错。但问题在于,如何学习,怎么赶超?在哪个层次上学习,在何种意义上赶超?
如果不是苛责先贤,我们大致可以说,在对西方学术的学习上,一些早期现代学人不很认真。一方面,人们在口头上唯新是举,以通晓“西学”为荣或自傲,但在学术的层面上,却始终对西方学术没有下过过硬的功夫。李幼蒸指出:“不论是陈独秀还是胡适,他们都不想先潜心学习西方理论,而是急于把一时知解(一知半解)马上用来结合‘中国之实际’。结果在世纪初的中国,所谓西方理论不过成为一种社会行事的招牌而已,其中又有多少深入的了解呢!”当然,学术研究要求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西学研究。但在此之外,学人们在认知的层面上,也的确有所偏差。
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在经过长期的封闭之后,如何面对西方学术,尤其是现代西方学术,就成了一个要紧的问题。李幼蒸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因此他的一些观察和思考,纵使有可能的偏颇之处,但仍具有其重要性。在一个落后封闭的文化环境中,人们在口头上对西学的重视与其实际的学力之间,形成极大的反差。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们实际上根本就不具备真正的学术判断力。正因为如此,人们对洋学历的崇拜,自然就顺理成章了。李幼蒸反思道:“外国人文学博士,在外国只是一个非常起码的基点(秀才而已),但由于崇洋媚外的态势,回到国内立即成为‘状元’。如果名利为心,洋状元必然要援引国际关系来巩固国内学术权势和通过‘建立学派’来‘扩大影响’。结果,‘学术权势观’逐代蔓延下来,腐蚀着几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哲学家’。”
“崇洋媚外”的逻辑延伸,是对海外学人的崇拜。在一个意义上,海外学人的学术研究,因其开放的环境,确有其值得学习的地方;而且在事实上,也对三十年来的中国人文学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也应该看到,海外学人亦有其内在的限制,他们对西方学术的研究并不深入。李幼蒸对此有相当极端的表述:“海外‘新儒家’的历史和哲学运动,几十年来抱残守缺,如今妄图以其落后的思想介入内地正在建设中的新学术思想世界。他们实际上是西方汉学的附庸,根本不必认真看待。”另外,正如李幼蒸在此书中多处提出批评的,是在海外学人中所普遍流行的学术民族主义;而学术民族主义因其封闭性,必然对学术现代化产生有害的影响。
与崇洋媚外相配套的,绝非对西方学术的积极研究,而其实是抱残守缺。而抱残守缺的基本策略,即无论面对任何西方学术理论,我们都能通过一种简单的类比,而将其视为“古已有之”。李幼蒸举例说:“如果把古典注经学换称为中国解释学,就像把易经学换称为中国符号学一样,都是炎黄子孙‘古已有之’的自大心态的产物。今日学界如果这样参与中西对话,借以强调中方学术传统的优越性,就难免自欺欺人了。中国解释学和中国符号学的提出是要求全面推进中西学术理论的对话,为此首先要强化西学准备,而且这个西学要比一般西方博士阶段的正规课业深广得多,是须下大力气用功的。”
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或可问,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术而言,西方学术占有怎样的地位?是否如有些学者所言,西方学术早已没落,而我们只有“返本开新”一途?李幼蒸指出:“现代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学术建设的重要性,可以说,甚至大于对西方社会的重要性。直到现在,连西方学者都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会对西方理论如此有兴趣。的确,现代西方哲学对中国的意义,从某一方面说,可能还要超过对西方自身的意义。这并非因为现代西方哲学内容本身的持久性价值,而是因为它作为激发现代化理论思考的‘工具作用’。”如此,则那种所谓的“复古”倾向,其实意味着偷懒和不负责任。
针对学术上的民族主义,李幼蒸指出:“20世纪,以至21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学术种种方面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认真消化西学这个庞然大物。你有‘博大精深’,人家也有‘博大精深’,而且今天是你沿着人家的‘博大精深’在前进,而不是相反。”而且,“‘西学’并非‘属于’西方,学术是天下公器,而任何地区产生的学术成果,最终都只能是属于全人类的。”
二
在西方学术中,哲学曾占有基础性的地位。在中国,人们对待哲学的态度,一方面是过度的尊崇,以致人们忘记了哲学所倡导的理性精神。但另一方面,在相当多学人那里,其实对哲学抱有极深的成见,在内心中是持拒斥态度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哲学所固有的难度,使那些未经严格训练、不得其门而入的人产生了一种嫉妒的心态;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实践中,对哲学错乱使用而败坏了哲学的名声。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即哲学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对那些习惯于生活在“潜规则”之下的人们,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和挑战。
而到了现代西方哲学那里,总体上对之前的哲学均有所批判。这其中有相当大合理的部分,比如李幼蒸所指出的:“历史上,哲学确实曾经是人类知识的主体和理论基础,而一两百年来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现代化发展,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身份和功能。今日残留的哲学中心论,貌似深刻严谨,实乃对人类生存经验的简单化、浪漫化处理。哲学必须满足于作为人文科学大家庭一员的身份,不可再‘幼稚地’以为各种玄学话语仍可称为其他学术之‘逻辑基础’。经此认识论调整,哲学功能和使命亦将焕然一新,并得以继续在人文科学大家庭内担任部分的‘领导’之职责。传统哲学理论和符号学的跨学科理论,亦应展开更具成效的互动关系。”“人类的知识绝对不是像19世纪以前的德国哲学家那样看作是一个由某种逻辑性的钢筋水泥加以固结的、‘铁板一块’的统一系统。”
的确,任何一种简单化的理论模式,在处理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的生存经验方面,均有其内在的限制。无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则不过意味着一种天真或幼稚。哲学中心论不足取,数理逻辑中心论亦不足取。十九世纪末以来,数理逻辑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一大批学术成果。数理逻辑所取得的极大成功,使一些人相信,只要掌握了现代数理逻辑,就能保证思维的严格性。但这的确不过是一个误解,正如李幼蒸所指出的:“数学推理的‘确定性’和伦理学和政治学内推理的‘确定性’,在构成和功用上是完全不同的。有人以为掌握了现代化的数理逻辑,就能在各个领域强化思维能力,这种简单化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正相反,很多在数理领域一流的人士,在社会人文领域内的思维能力,不仅不一定优秀,甚至于还会经常犯‘逻辑性’错误。”
尽管我们说简单化的哲学、数理逻辑中心论不足取,但仍有必要指明的是,无论是哲学还是逻辑,它们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所取得的诸多重要成果,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李幼蒸在谈及自己的学术脉络时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有一个从哲学到理论的转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与当代西方主流学术思潮有一种内在的同构关系。而且事实上,在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议题中,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即任何看待人文学术中的理论研究。李幼蒸指出:“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经验性和理论性的互动关系长期存在。在非西方学术传统中则普遍欠缺这种互动关系。如果要在东亚文明传统内促进理论性和经验性的互动,必须首先促进东亚学术传统和西方学术传统之间的互动。但是存在于西方的东亚学和汉学的学术主流和中国国内的国学主流一样,都是经验主义方向的,包括其传统的‘玄学’,后者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理论性研究,而是具理论性外表的另类‘诗学’论述。”
中国当代学术中理论研究的长期阙如,使不少中国学者有一种反理论的心态。而这样一种心态,反过来又封闭了自我,使其在理论方面缺乏基本的判断力。这样一种因缺乏独立研究而表现出的对新理论的趋从心态,在一些坚定的学术民族主义者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我认为摆脱这一尴尬境地的恰当做法,是鼓励独立的理论研究,只有如此,我们才不至于在面对西方的新潮理论时进退失据。但我这里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那种只有姿态而无多少实质性内容的泛理论性研究,在学术上有多大意思。
三
以什么样的动机来研究学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问题,有两种极端的回答。一种是过分看重动机,并以动机是否单纯来作为评定学术优劣的唯一标准。这样一种道德主义的评价方式,严重低估了学术创造中的复杂性,且在相当的程度上鼓励了一种平庸的伪善。因为在那种一种氛围中,人们可以以所谓的学术真诚来掩盖其实质上的平庸,从而对有效的学术竞争形成阻碍。针对此一道德主义的学术评价方式,我们可以说,过分看重动机是不必要的,而应该看是否创造了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这一评价方式的转换,意味着在总体思路上,从注重动机转向了注重后果。
而凡事看后果怎么样,即功利主义的思路。在当代社会,功利主义是占主导性地位的思想潮流,它不仅在社会经济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亦渗透进人文学术领域。李幼蒸就此指出:“……现代社会人群倾向于‘求成成功’大于‘求理求义’。于是任何一种方向上的历史行为选择,都可能带有学者个人和学派集团巩固自身利益的势头。这样的势头如足够强盛,必然倾向于广义的党同伐异,其结果将不利于社会学术思想的发展。”
而且,更危险的地方在于,这样一种以追求成功为导向的学术研究,绝不只是某种地方性的暂时现象,而已成为全世界流行的通则。李幼蒸进一步揭发说:“今日人类的学术真相正是:利益取代了真理。学术批评触及此权威学者心迹之真实,即被视为在‘损害名人利益’。真理之辩,遂成了利益冲突和斗争的策略之学。辨析真理的知识条件问题,也就转化为名势大小的经营学问题。传统的乡愿辈之智术,在社会现代化之后,也就商业化、制度化和效率化了。”
人文学术领域的功利主义思路,意味着对人文学术的深度伤害。这与人文学术的特质有关。我们或许可以相信,一个心灵迟钝的人,有可能凭借其智力优势和勤奋,在技术领域取得较大的成功;但我们的确难以想象,一个因热衷名利而心灵麻木的人,能在人文学术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其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人文学术研究要求其从业者至少在研究过程之中,保持其心灵的敏感性,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进入他者的心灵,解开其心灵的密码。人文学术研究的难度和魅力,亦正在于此。
而单纯看重学术成果的学术评价方式,其实意味着对心灵的遮蔽。从这个角度看,人文学术评价中的功利主义思路,其实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短视症。针对这一现状,剖析学人的心迹,就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正如李幼蒸所指出的:“学术心术的重要性不在于褒贬学者之间的道德高低,而在于它足以妨碍社会人文知识的进步。学术理论方向之‘始原’正在于学人之‘隐蔽心迹’。”
但相当遗憾的是,在学术功利主义的主导之下,此类反思甚至难逃迂腐之讥。李幼蒸自己就说,“在今日法治社会,我言种种,毫无意义,必遭西人笑掉大牙:何人不是在赛场上实行‘合理冲撞’?民主社会就是保障大家追求合法之私利。就社会经济等层次,果然如此。但学术思想层次,必不能如此。学者如果以商人方式行事,其学必不能进。”但在我看来,针对此种反思,笑掉大牙的又岂止是“西人”呢?或曰,我们都早已成了“西人”?
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在此种不良的学术背景之下,未能得到足够关注和深切反思。李幼蒸批评道:“最让人失望的知识分子往往就是一些哲学家(实际上是‘哲学话语运作者’而已)。因为他们的工作对象和表现手段都是‘道义话语’,于是会使人们误以为他们代表着良知和希望。然而实际上他们所做不到的就是‘知行合一’,他们也很难做到表里合一。他们一些人只能‘说道义’,却不能‘行道义’。这样,人们还能把哲学家都成社会的‘良知’么?实际上,不分国内外,存在着一个二十世纪哲学家们集体检讨自身的必要。萨特和海德格,难道不需要做这样的‘自我批评’么?但是,他们宣称‘哲学家’是永远伟大的,是用伟大道义语言指导社会的。他们是么?”
据我有限的了解,在西方学术界,人们对如上哲学家的道德过错,已有深度剖析和批评,尽管可能并不充分。但在中国,不少学院中人,却倾向于对他们所爱戴的哲学家们持一种“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我不知道他们在何种程度上“理解”如上哲学家的所言所行,又在何种意义上持有一种“同情”的态度,而不只是通过推重所谓的大师名流,并以此来证明他们自身的无知和渺小。
四
在此书中,李幼蒸在关于学术的多个层面上,对相关问题提出批评。有关学术与政治,中外学人多有探讨。而在今天,知识分子在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回忆之中,亦多强调其自由和开放的一面。我想这可能也是事实。但在此种回忆中,其实考虑较多的是政治层面的东西,而在学术层面上,那种以议政代替研究的学术倾向,却较少被提及,更遑论反思了。李幼蒸指出:“而80年代学界人士,在谈论社会性哲学问题时,习惯于直入历史表面现象,品评是非,而对相关的学理分析条件,则不甚措意。结果,直接的话题本身不过成为个人感受经验的一种宣表:表面上似在讨论分析,实则只不过在变相地重复着对话题的关切而已。在此话语性重复的过程中,说者和听者均重温着自身已知的有关话题本身:于是‘谈论’现象本身,被当成了正在‘研究’此现象。”
我想,在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总体性的金色叙事中,李幼蒸的上述批评,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那样一种时代性的思维习惯和学术倾向,在今日占据主流地位的一些学人身上,有着格外鲜明的体现。
事实上,将严肃的学术话语和通俗性的学术话语混为一谈,不过是追求学术功名的一种有意操作。李幼蒸批评道:“在文化落后的环境中,对于重名利追求的广大读者来说,是根本不想、也没有能力来区分严肃学术话语和通俗化学术话语的。而且就这样的环境和这样的行为动机来说,学术理论一直被用作间接追求名利权势的工具。当然这类追求都包含在社会道义话语之中,从而加重了而不是减弱了,学术功利主义动机:社会道义形象成为学术名势追求的掩护。”
与对上述诸问题相连着的,是对知识分子本身的批评。李幼蒸提到,“重资格资历,可谓海外华人的共同心态。这是古代功名观的现代翻版,足以成为新时期中华民族学术思想前进的障碍。”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其与体制之间的暧昧关系,更使其常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李幼蒸指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身份,使他们有时不免言行失宜。正是这个曾经使他们吃尽苦头的旧系统,也是把他们一下子从1949年前的普通知识分子‘拔高’到等级制度高层的根源。他们也因此提拔而有了高人一等的意识。加以意识形态管制趋严,中央地区的高级人文知识分子突然成为垄断资讯的‘独享者’。地位、名气、资源的特权享有身份,是旧时期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生存史上的另外一个侧面。”
我们当然可以说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的主要罪责,当在霸道的权力一方。但我们亦因认识到,思想改造之复杂性的一面,是知识分子在面对权力的驯化时,其半推半就的复杂心态。这样一种在权力面前的懦弱性格,反映在学术层面上,即我们的学术界,流行一种类似梁山好汉般的排座次的风习。李幼蒸对此指出:“我们的学术界,百年来,遂造就了一大批‘学术菩萨’。学术活动,就成了制造学术菩萨的运动:对各种‘大师’进行崇拜、排座次、安排势力划分、将其一一纳入民族学术‘先贤祠’,以作为民族集体崇拜祭祀的‘偶像’。做学问的最终目的,成了为大师定尊卑的活动。在此趋势下,还有什么真理可求呢?其治学目的不在于求真理,而在于通过拜学术菩萨来分沾名声势力。”一方面是算计,一方面是懦弱,但在这种内在的势利行为的背后,其实是人格独立性的缺损。
五
学术之要义在求真,这似乎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理解。但问题在于,在许多现实的条件下,我们对此的理解,却又往往不过是将其视为一个口号;口号当然可以高调,但没有任何可操作性。而之所以没有可操作性,是因为现实有种种制约,阻碍我们去求真。可见,求真的前提,在自由。而自由的核心,是自主性,换一种说法叫独立。但对于学者而言,体制固然能为其提供种种便利和舒适的生活条件,却在一个极严重的意义上,侵蚀着学者的独立性,尤其是在面对一个坏体制的时候。
李幼蒸之所以能在其回忆性文字中提供如此深刻的反思性批评,我想与其颇具传奇性色彩的学思经历密不可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中,其与体制的关系,均处于相对疏离的状态;也正是这样一种疏离,使其获得了一种难得的边缘视角和自由心态,从而促成了其在暮年的自由言说。的确,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一些具体观点,但我想从他这样一个人的经历和遭遇出发,来激发我们思考真理与体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是一个极富现实意义的思想论题。而无论我们如何反思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体制所具有的那种垄断真理的强劲冲动,在一个最低的限度上,亦应保持应有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