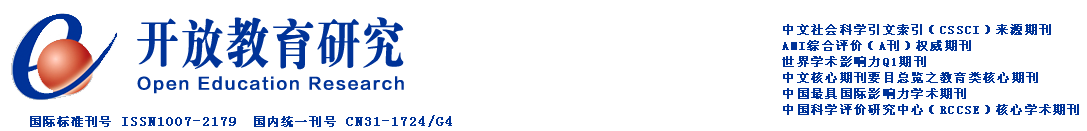2002-02-19 来源:光明日报 本报记者 夏 欣 我有话说
朱学勤,1952年生于上海,历史学家,人文学家,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
曾就读上海高阳路第一小学、继光中学,初中毕业后赴河南兰考县插队落户,后在化工厂做过管道工、厂办中学教师。改革开放后以同等学力考取研究生,陕西师大历史系硕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
记者:这一阵人们围绕“剽窃事件的议论不少,据我所知,这类事情仅2001年一年里被媒体曝光的就有十几起,你觉得这给教育界哪些警示?
朱学勤:屡屡发生这样的事,当事人确实应该有深刻的反省,但我不赞成光把火力集中在个人那里,穷追猛打,教育行政部门也该想想自己的责任。更多的责任是在体制。
现在一些大学争发“大票子”,“票面额”在扩张,“含金量”却在猛跌。所谓“大票子,指两头都在扩张,一是教师,二是学生。从教师这头说,“教授”不到头,教授之上还要“硕导”,“硕导”之上还要“博导”,叠床架屋,这种现象导致学术职称严重贬值;学生中高学历“泛滥,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缺少,教育界“头重脚轻。本科毕业生作为知识部类里的通才,本来应能满足就业市场的基本需要了,但现在本科教育正在降为就业市场用人的底限。这样一来,“博导”也不过是“教授”的含金量,“教授”则降格为“讲师”,而“学士”也再向下降格。
造成教育“大票子现象,我认为有两个因素:一是学校行政权力干预太甚;二是学术评价体系严重扭曲。这两者本身又互为因果。行政权力干预过甚,使得教育出现新的“大跃进”,到处争办一流高校,争“博士点”,争“国家重点学科”,全是“一流”,还有“一流”吗?在这样的情势下,我若是大学校长,也不能免俗。这些校长、院长既是催问者,也是被催问者,有点类似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普通教师更是让数字、表格逼着走,搞得人心浮躁,出现一些恶性竞争。
在这样的氛围下,教育的学术评估体系怎么能正常?有些青年教授一年出一本书,“十年磨一剑成了“一年出一书,哪有做学术研究一年出一本书的?这又不是写小说。
记者:除了大家说得比较多的道德自律方面的事情,就学校环境而言有哪些抵制学术浮夸的办法和机制?
朱学勤:学者自有学者的工作周期,有积累,有突破,有高潮、有低潮,起起伏伏,很正常。行政权力要做的,是给学术发展搭建一个平台,像搞经济先要搞“三通一平一样,而不是总在那里定指标,要政绩,急着“催化”什么。行政干预太多,经济就发展不起来,教育也一样。至于职称,我以为还应按照原来简朴的做法,做减法,不做加法。如果能在教授中拉开等差,把正教授分一、二、三级比较好,不必搞什么“博导”、“硕导”。
记者:再说学生方面。毕业生的高学历膨胀客观上也有社会就业压力的影响。
朱学勤:可是高学历者多没有能从真正意义上缓解就业压力,而只是把高中生变成本科生,把本科生变成硕士生,多花三、四年钱,只把本来就存在的就业高峰向后延迟了三、四年。有些就业单位似乎总是想要比需要的学历高一级的学历,去报社、出版社,甚至党政机关,都要求进博士、硕士,这样一抬,使大学本科生很难找工作,把本来应该到大学为止的“学历教育,再拔高到研究生阶段,无形中把“专才教育变成“通才教育,而合格的中、高等专科人才严重不足。报载深圳人才市场上高级技工与硕士一样待遇招聘,市场已经对这种现象亮出黄灯了,说明操作性技术较少受到重视,这在高校教师中也是如此。
记者:大学教师也要讲人才的多元结构?
朱学勤:大学里有不少人才,所谓“大学的实力在‘大师’是对的,但是教师不能都是“只有设计的头脑,没有灵巧的双手,要形成人才的梯队。不久前有报道说,现在一些美术学校毕业的人全都考大学去了,一些绝活在一门一门面临失传。发达国家对专门技术十分重视,比如在综合国力强大的德国,受中等职业教育的人就业后的报酬、社会重视程度并不比大学毕业生差。我早年在工厂的时候,一个八级钳工得到的待遇和尊重一点不比工程师少。碰上书本里没有答案的疑难怪症,一圈子工程师束手无策,现场只听得厂长对着电话里喊:“快,快叫‘段八级’来,派车接,把他从被窝里拉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