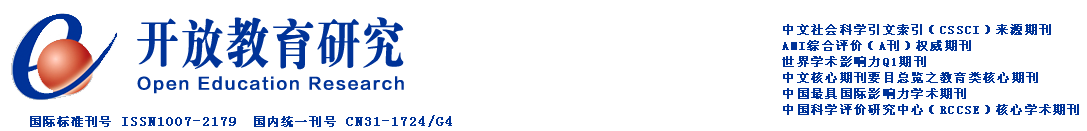昨天在 [学术中国] 微信号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施一公教授的一句话,他说“自然科学期刊所发表的论文,99.5%对促进学科发展毫无关系。”虽然也曾思考过学术在当下这个世界的意义,但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还是震了一下。尽管这个数字只是施老师的一个估计,但反映得却是当下学术界尴尬的事实。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就更不用说了。记得很早之前有个形容国内社会科学现状的段子,说把国内70%的社会科学书籍烧了,对社会科学发展不会有任何影响。不知道职业知识分子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会作何感想?人类精神的最大苦痛莫过于:你倾注了全部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到最后却发现,它对这个世界毫无价值。
记得读本科的时候,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名是《以学术为业》,作者是马克思·韦伯。文章写的什么,现在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但是大概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认为:“以学术为业”是一件非常祟高的事情。我们这一代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人,大概是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仍然植根在集体主义的土壤里,却绝大部分没有经历过父辈们的饥饿和贫穷,在改革的号角之下出发,迎着曙光,追逐着不知道要去往哪里的理想。像穆斯林去麦加朝圣一样,学术之于我们,那是需要顶礼膜拜的信仰。
然而,当我们逐渐深入这个社会,便会不情愿地发现:学术所有的意义,仅仅在于它可以成为我们自己阶层晋升的阶梯。放眼看看如今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们,有多少不是底层家庭出身?当一个社会模式不断走向稳定,阶层就会不断固化。而这个时候,学术之路相对于其他的道路来说,要相对地多一些自主性。没有关系,没有背景,向前望去,所有的路都是黑洞洞的。相比之下,学术这条路,还有那么一丁点儿缝隙还可以让你只需要靠努力就能争取,尽管这点缝隙也在不断地缩小。英国纪录片《人生七年》中那个唯一的特例尼克,他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了一个大学教授。是啊,多么 滑稽,他只能成为一个大学教授。
八年前,宿舍窗户斜对面的一个师姐在宿舍里安静地自杀了。她死后,我在她的博客里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学术、思想:写在青春的边缘》,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这一切有何意义?做学问有何意义?解决一个理论问题有何意义?出一本书有何意义?对于我们这样一群从社会边缘起步的人,最初的求学无非是无望中的人生出路吧。学术在于你的最初,其实无异于市场中的竞逐。只是困顿过后的生命释放,如同一个自我证明的游戏。而所有追逐太阳的奔跑,都容易指向乌有。我们当初播下的龙种,可能只收获了跳蚤。如今,当心气减当年的我站在这儿,回望当时的妄为与冲动,又是怎样的自愧难当呢。”
是啊,有何意义?可这些无意义难道不是一开始就注定的吗?所有上路时那些不纯粹的初衷都起了作用:因为生存、因为成功、因为不服输、因为听话……..唯一没有因为对这个世界不可扼杀的好奇。我们曾那么努力地想去通过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到最后却身不由己地陷在竞争的漩涡里不可自拔。
为了生存和实现自我而出发,对于除学术之外的任何一个行业,都没有问题,甚至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当以学术为业,奋斗便是一种灵魂的折磨。因为你终究会发现,奋斗根本无益于学术。卡尔·波普尔在《关于音乐及其一些艺术理论问题》中说,“要想走在时代前面”的意愿根本无补于音乐,也无益于真正献身于自己的创作。这对于那些仍然在在学术路上爬行的俗人来说,简直就是戳在了心口上。
当学术成为一种生存的手段,像其他职业一样充满竞争,它还有多少真正的价值?职业知识分子是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出现的。是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才使那些长于思考的人解放出来。源于身心闲适而产生的职业,如今却像市场里的商业一样在竞争下生存,为学术而学术,为成功而学术,这本身就是一种南辕北辙的背离,注定很难有价值。而懦弱的知识分子们,很少有胆量去突破既有的格局,不自觉地一代一代堆积着这种无价值。
前两年,当我看到安兰德在《致新知识分子》里的一段话时,瞬间泪流满面。那段话是这样写的:
“一个世纪以来,在知识分子这个职业看不见的地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悲剧、绝望和无声的毁灭——在这些从业者的灵魂深处——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类的未及发挥的潜能和诚实在这些潜藏、寂寞的冲突中被毁灭。进入这个智识领地的年轻的心灵怀着一种参加圣战般的复杂感情,为如何成就一种有意义的人类生存寻求理性的答案,结果未能找到哲学的引导和领导,却发现那不过是哲学的骗局。其中有些人在绝望和不平的愤慨中放弃了这个观念的领地,消失在主观性的沉默中。另外一些让步了,眼看着自己的热望变成酸楚,自己的追求成为冷漠,自己的圣战变为一种愤世嫉俗的行当。当他们接受了启蒙领导者的角色时,他们就身陷一种长期的焦虑中,就像是骗子时刻害怕被暴露一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知识只是建立在一团浓雾之上,其惟一的有效性完全依赖于某个人的感觉。”
安兰德这篇文章是想表达由于哲学出了问题,使得一切学科都失去了方向。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哲学的问题导致了学术无意义的结局,但她半个世纪前所描写的这种情况,至今好像并没有什么改观。大部分的学人,仍然是“开始自己的事业时并非平庸之辈,但结束之时却成了自命不凡的庸人。”更遗憾的是,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安兰德这样的思考力和勇气,傻子和疯子才会自己砸自己的饭碗,所以,这个世界就这样看上去皆大欢喜地传承着。
去年的最后一天,我坐在桌前,写下一些文字,其中一句是:
“我希望/ 自然多给人类一点时间/ 从愚昧中觉醒/ 停止喧嚣 回归理性/ 让文明重新启航”
写完之后,掉头打开论文,又开始去敲那些对这个学科可能没有丝毫实际价值的文字。不同的是,再也没有多年前朝圣般的心情,仅仅是为了自己,不得不去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我们最终的学术,只是在“学术理想”和“现实生存”之间达成的一种妥协。然而维持这种妥协的均衡都很困难,大部分人终将沦落为一个“学术工作者”,以“学术”的名义,终日忙忙碌碌,浪费资源,却对追寻真理没有任何价值。只是在偶尔不经意的一刹那间,脑子里突然又跳出改变世界的冲动,紧接着又湮没在一堆俗事中。
可正是这个偶尔的冲动,支撑着我们以学术为业,在与现实不断的对抗和妥协中慢慢地爬行,梦想有一天,可以看到更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