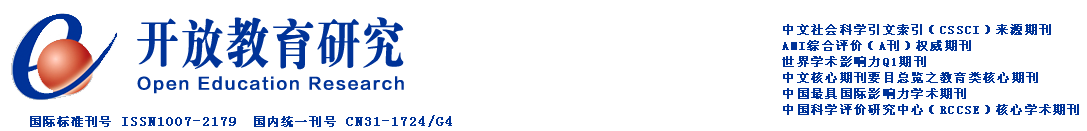很多人认为所谓“中国特色”是相对于西方话语而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之所以没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为一直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鹦鹉学舌,从来没有自己的一套概念、范畴和思考方法,甚至提不出自己的问题。
核心提示:“中国话语”的意思就是切中当下中国人生存经验、切中真正的中国问题、对中国问题有诊断力的话语,至于这个话是中国人说的还是外国人说的,古人说的还是今人说的,是在中国大陆说的还是在美国说的等等都无关。
一个真实地生活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中,直面并能够自由、直率、真实地表述自己的生存经验、生存困境的话语,一定是中国自己的话语,不用专门去冥思苦想什么中国特色。
1、“中国话语”“中国特色”是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界,也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热衷于谈论的一个话题(在社会学界更多地叫“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这个话题明显地是针对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西方影响的。以文学研究为例,大约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曹顺庆先生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者开始讨论所谓中国文学理论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失语症”。他们认为,中国文论和文化近代以来在西方影响下失去了我们自己的话语,“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等)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并强烈呼吁应该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以便在世界文论中有自己的声音(曹顺庆的《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东方丛刊》1995第3期,总第13期)
对“中国话语”“中国特色”之说,我一直持有疑问。其中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所谓“中国话语”到底是什么?
最可能让人直观地联想到的答案是:“中国话语”就是中国说的话语,好像“中国”是一个会说话的主体。但“中国”当真会说话吗?真有“中国”这样一个说话主体么?
从政治的角度说,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从地理的角度说,中国是一片版图,从人口的角度说,中国是14亿中国人的集合体。这些意义上的“中国”都是不会说话的,因此当然也就不能把“中国话语”理解为中国说的话语。说话的主体必然是、也只能是一个个具体的中国人,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也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当然,我们在一些外交场合、外交辞令中的确会听到“某某国家的声音”“某某国家的立场”这样的说法。但这些说法的真实意思是:这是代表某某国家人民的声音或立场,又由于“人民”本身还是不能说话的,因此,“人民”的声音通常必须通过官方机构也就是政府来代表,它是由官方指定的发言人说出来的。这恰好证明无论所谓“国家”还是“人民”,本身都不可能能说话。所以,它的声音只能通过政府指定的代表来发出。如果这个政府是人民民主选举的政府,那么,这个代表就是合法的,否则就是不合法的。有些以“中国”名义说话的人或著作,其实是窃取了“中国”的名义。比如《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这些书中的观点其实只是代表作者自己,最多也就是部分中国人,他们的代表资格是自封的(“中国不高兴”的说法尤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中国”是一个有感觉器官的人吗?它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吗?“中国”怎么会不高兴?或许作者的意思是中国人不高兴。但这个说法也很可疑:中国有13多亿人,他们每个人都不高兴吗?难道作者进行过全民民意测验?)。
因此,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不可能是“中国”说的话语,也不可能是某个代表“中国”的学者说的话,因为没有谁有这样的代表资格,可以声称他的话语就是“中国话语”。如果说我们可以在政治上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一个政府,并由政府指定一个发言人代表中国说话,那么,学术研究却绝对不可能这样来选择或指定“中国话语”的代表。
2、另一个思考“中国话语”的思路是: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即使说话的主体是一个个具体的学者,但是如果他的话有“中国特色”,那就是“中国话语”。但问题又来了:什么是“中国特色”?标准是什么?就目前的情况看,很多人认为所谓“中国特色”是相对于西方话语而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之所以没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为一直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鹦鹉学舌,从来没有自己的一套概念、范畴和思考方法,甚至提不出自己的问题。这个意义上的“中国话语”带有以中国为本位进行思考和言说的意思。
我承认这个思考中国话语的思路相对而言有意思一些。但同样有不少需要澄清的问题。首先,以哪个中国为本位?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当代中国或当下中国?答案显然是当下中国,因为中国(不管是它的社会还是文化,政治还是经济,民俗风情还是日常生活)是一个变化着的国家,某些古代中国的特色已经不再是当下中国的特色了,比如纳妾和裹脚,比如格律诗词(不是有很多批评家说张艺谋那些展示中国古代风俗的电影不能代表当下中国么?);同时,某些来自古代,但依然能够代表今天中国的传统,也一定还活在当下、存在于当下、包含于当下(不管是鲁迅先生批判的“国民性”,还是今天我们说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再不加区别地恢复古代的学术概念和方法,拒绝使用西方的或现代的学术概念和方法,想借此来解释当下中国并建构中国话语,我以为无异于缘木求鱼(很难想象可以用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和方法可以解释当下中国的文学)。
既然“中国话语”就是中国特色的话语,中国特色又只能是当下中国的特色,那么,依据我的理解,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就是切中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切中当下中国的真问题、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政治和经济、文化艺术和日常生活有诊断力、解释力的话语,这样的话语才是有“中国特色”的。至于这个话是否包含了西方理论或古人理论,是中国本土学者说的还是美国学者说的等等,都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它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