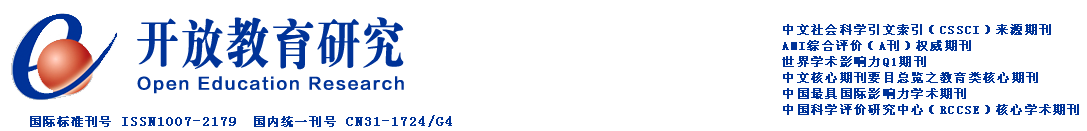现代性与前现代的各文明之间的普遍与特殊,或不如说一与多的关系,是现代思想兴起后的老问题了。此问题不断被提出,这恰恰意味着,人们还没有形成共同的不移之见。本文不拟为众说纷纭再增新议,而是更倾向于,在直接正面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对问题的形态、背景和相应的诸方法论做一宏观的观察。这或者有助于做出较成熟的权衡和抉择。
现代性之一与多的关系,对于现代性在其中最初显露与成熟的文明来说,似乎是不成问题的。对于通过对外关系(无论经贸、外交、战争等)被动卷入另一文明之扩张过程的诸文明来说,这却构成了首要的思想问题。在那里,现代化的压力与处境,表现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意味着对本位文明本身的“挑战”。因此“挑战-回应”模式不仅运用于中国,而且似乎也为一切前现代文明的非原发的现代化历程提供了基本的叙述框架。由于西方文明首先孕育和发展了现代性,而其他文明被迫但是无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那么可想而知,其他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似乎不仅是特殊文明之间的关系,而是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关系,或至少是学生和先生、模仿与原型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的基本脉络——所谓古今中西问题,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一切前现代文明面对扩张的西方的共同焦虑。这一焦虑的根本,在于以下两个判断:西方文明不仅是某一特殊文明,而同时是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一切人类文明的共同归宿。因此,西方是现代的起源,也是其他文明的目的。所有其他文明的历史,都只是现代性之史前史。用现代性作为衡量标准,处于史前史的“文明”,其实是“野蛮”而已。
这一历史观的背景是现代文明的全球扩张。15世纪以来,现代文明就处于一种增长和扩张之中。直到18世纪末,主要在19世纪,殖民主义时期的现代文明才开始越过西方文明的界限,把贸易之外的东西(即由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内容体现的现代“文明”内容)送到了非西方文明之中。所谓现代文明与诸前现代文明的一/多问题,所谓“挑战-回应”模式,即属于现代文明的世界性扩张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前,现代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仍未结束。然而,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情况有了改变。自15世纪以来,西方文明从未象现在这样,不再垄断现代文明扩张的动力源泉。如果说,现代文明的世界性扩张曾为非西方文明带来了严重的文明“挑战”,那么20世纪末以来,它同样为西方文明带来了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在冷战结束后一度表现为胜利者的孤独茫然,表现为无聊沉闷的历史终结感。但在今天,随着中国和其它非西方文明的崛起,它更多地表现为对丧失现代文明扩张主导权的焦虑。
形势的变化促使我们重新反省“挑战-回应”模式、努力换一种方式思考现代文明的一、多问题。在这个方向上,本文尝试提出一个主要观点,即将现代文明、西方文明、资本主义三者当作彼此交叠但不重合的历史范畴。这三个范畴的错位处,就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头等重大的世界历史时刻。非西方文明或社会主义理想所期待的光荣时刻,正是现代文明与西方文明的错开时刻,或现代文明与资本主义的错开时刻。而非西方文明面对现代化压力的特殊性焦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于对此三个历史范畴的重合式理解。篇幅不允许给出系统的论证,这里仅提出以下几条意见。
首先,显而易见的是,西方文明并不等于现代文明。西方文明有它自己的古今问题。无论西方思想家将现代性追溯到古代西方文明中的某些要素(例如海德格尔追溯到技术、韦伯追溯到合理性、施特劳斯追溯到自然与律法、哲学与城邦的关系等等),仅仅这些要素不等于现代性。它必须在其它历史条件下,才能作为现代性的要素起作用。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决定性的。在韦伯那里,新教传统占据了同样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西方文明传统中,也有克制这些要素的力量。西方文明本身之于现代文明,也是一个特殊文明。现代性起源于西方文明,这并不意味着,它同样会终结于西方文明。中国与印度的崛起为现代性的结局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与其将西方文明整体上等同于现代文明加以崇拜或者批判,不如致力于研究现代性本身是如何孕育和脱胎于西方文明之内的。
其次,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那些踏上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文明”,其多重传统中同样具有某些潜在因素,可使其现代化免于被动的“回应”模式。在概括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来历与前景时,深受韦伯影响的学者们乐于寻找儒教与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对接之处。甚至福山也在追溯中国崛起的历史渊源时指出,秦汉以来中国政府的治理传统中有着强大的现代要素。平心而论,中国政治制度中后封建的绝对主义皇权特征、皇权之下的非贵族官僚制度、平民精英的教育/选拔程序、以及儒家传统中的温和理性色彩(非宗教神学色彩)甚至革命改制学说等都是非常现代的。在西欧,这些东西要到文艺复兴之后,乃至18、19世纪才逐步出现。其兴起过程中也不乏对中国的赞扬和学习。如果被粗鄙的西方中心论遮蔽了这些,那势必认为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高度相似,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历史障碍是“封建专制”、是“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现代化是“走出中世纪”,这就既不能解释中国现代化的成就、速度和特点,更无法给出人类现代性别样的未来。
然而,第三,现代性要素、现代性思想、现代性的某些特征,所有这些都不等于完整的现代性和现代文明。没有资本主义,现代性大概只能停留在思想革命阶段。现代文明与现代思想的差别在于,资本主义将科学与资本结合起来,既需要知识本身的再生产也需要同时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条件和结果的现代市场、市民社会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再生产。我们称之为现代文明的一切,从历史内容上看,无非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真正在全球扩张的不是现代思想,而是流动的资本。所有其它东西都是资本之河上的漂浮物。给予非西方文明历史创伤,并将之拖入全球市场的,不是新教伦理或伽利略物理学,而是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形态——殖民主义。现代文明的“普遍性”,不是西方文明的普遍性,而是资本、市场、价值规律的普遍性。所有的文明都是特殊的,但世界市场只有一个。所有的文明都有一个“本地”,但资本可以在全世界流动。而现代文明,这个人类唯一的“非本地文明”,随着资本流向各地。它诞生于某个文明,但绝不会被此文明束缚。所有的产品都是特殊的,但它们据以交换的货币中介则是普遍的。普遍是什么?普遍就是交换关系的根据。哪里有交换、兑换、翻译,哪里就有普遍性。没有同一个普遍意义,翻译是不可能的,没有普遍价值和象物理空间那样唯一的世界市场及其规律,贸易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绝不会被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任何文明所束缚。资本天生不受空间限制,抽象无形,超然于万物之上,又化为万物、创生万物、毁灭万物、为万物立法定则。它让有的民族兴起,让有的民族衰亡。资本在历史世界的神学普世性差不多相当于自然世界中的上帝。掌控资本最熟稔的那个民族正是那个数千年没有“本地”,但拥有人类最早唯一普世神的民族,这并不是偶然的。现代文明的唯一性不过是资本一神教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欲望和结果。西方文明的当前焦虑在于,面对这个它所培育的全球资本主义,它已力不从心。西方文明可能渐渐失去了对全球的强大控制力,但资本主义没有。它只是换个机车而已。
那么,第四,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分析的思想学说,都值得重新重视。这里要重点说说马克思主义。随着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特别是由于老派马克思主义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分析能力,马克思主义在当前只能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科学分析,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命运的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国和印度等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方中心论、削弱了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导权、加强了非西方文明的自信和自觉。但这并不会褫夺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比任何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更多地注重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对人类生活与交往带来的历史性影响。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力量所在。其具体结论或可科学地商榷,但这个视野对于考察现代文明则不可或缺。全球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析在保守主义那里是几乎是找不到的。自由主义则过于依赖市场与市民社会的神话。在柄谷行人这样对现实保持高度敏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注意到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独立性,虽然他给出的方案是浪漫主义的。
要之,在中国崛起的历史时刻,既要始终保持对各特殊文明的历史传统的同情理解与解释(这一点是各种版本的保守主义的长处),也要运用政治经济学与完整的社会政治学说观察和分析仍在形成过程中的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与各特殊文明之间的一/多关系问题,可以从市场、资本、市民社会之普遍一元,与文化与历史传统之特殊多元之间得到更多的启发。物质、符号与生活方式的再生产是一条基本的线索。而政治、国家、媒体和个人生活,正处在一与多的这种绞合与紧张之中。换言之,现代文明自身表现为符号与生活/交往方式的生产-再生产形式,同时也取决于物质再生产的形式。
跳过更详细的具体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如果允许我们扩大文明概念的内涵,将生产方式、市场制度等一切物质力量也收入其中,同时又保存文明之上层建筑意涵与物质力量的差别,那么现代文明可以被理解为双重的后者说两层的。在其底层,现代文明的物质动力层,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为自己创造出经济形式;在上层,被这种经济形式通过不同方式——即社会与市场发生关系的方式,市场对社会的影响和塑造方式——奠基了不同的符号与交往关系形式。现代文明之一元的普遍性,存在于物质生产这个底层,这是资本-市场-技术-劳动与经济交换的世界。而现代文明之多元的特殊性,则存在于符号与交往关系再生产这个上层。这是伦理、法律、政治以及公共舆论、审美、宗教的世界。是传统和各种新兴力量的鏖战之地。
这是前互联网时代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大致情况。中国崛起的时代也正是互联网社会经济崛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最根本特征是物质、符号和社会交往三者界限之扬弃。移动互联网经济学的本质是赋予这种扬弃以持续的技术动力和经济形式。物质生产成为高度符号性的(最高端时尚的物质产品就是各种符号的使用、接受和发送器),而符号拥有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力量。符号产物(作品、文本)从未象今天这样赤裸裸地和物质与货币结为一体。社会交往也随之高度符号-物质-抽象化了。在历史上,人类从未象今天这样接近于柏拉图的囚徒,他们所面对的“事物”,无非是符号和影像。随着符号/影象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越来越步调一致,现代文明的单一与普遍就会越来越压倒其多元与特殊。世界各地的文明城市面貌日益趋同,市民和游客的面貌日益趋同,昭示着世界历史不仅开始进入了科热夫所谓“普遍同质国家”(universal homogenous state),而且开始进入了普遍同质的社会关系、空间结构和心理状态之中。在黑格尔哲学那里,只有绝对才能真正终结历史。如果,一个集精神(符号、社会与自身批判)和物质于一身的绝对总体有朝一日最终出现,现代性文明无疑将成为世间唯一的文明。这意味着,现代文明的真正历史就此开始,而人类文明的历史将就此终结。
来源:《文化纵横》杂志